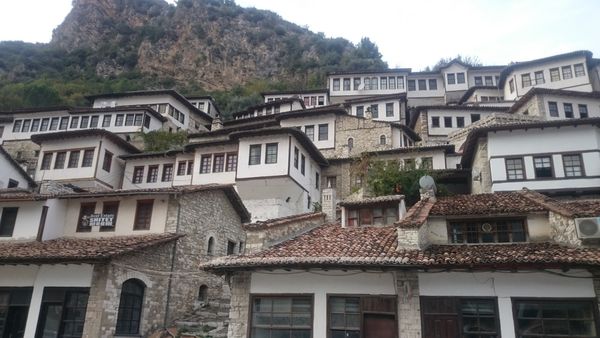阿爾巴尼亞人,還是馬其頓人?
「馬其頓有兩種人:馬其頓人和阿爾巴尼亞人。馬其頓人是人,阿爾巴尼亞人則像是豬一樣。」我坐在馬其頓一個小鎮咖啡廳的吧檯邊,與眼前這位來此打工的馬其頓高中生聊天,他竟突然地冒出了這一句話。
這裡的高中生打工仔們都很可愛,英文很好也很有想法,但我實在不是很習慣,當地馬其頓人,竟然可以這麼理所當然地仇視著阿爾巴尼亞人。
「我們在比賽的時候,阿爾巴尼亞的球隊如果輸了,他們就會大聲的叫罵我們,並且是用很難聽的字眼罵,甚至他們還會丟酒瓶,然後在牆上用噴漆寫各式各樣的髒話辱罵我們……」那位馬其頓男孩,隨後對我說他之前遇到「像豬一樣的阿爾巴尼亞人」的經驗。
馬其頓境內,如今大約有 30% 的人口是阿爾巴尼亞裔,主要集中在馬其頓的西半部,有些城市,甚至有超過半數的阿爾巴尼亞人。
然而,在這個國家內,這兩個民族的人們,關係卻似乎時常處於緊繃狀態……。
歷史恩怨,造就兩大民族長年仇視彼此
歐洲的巴爾幹半島,近年走過連年衝突、主權紛亂的歷史。 1991 年因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解體,正式獨立的馬其頓共和國,其領土內就包含了馬其頓人,和約 20%,長居此地的阿爾巴尼亞人。 1999 年,由於科索沃戰爭爆發,巴爾幹半島爆發近代史上的大規模難民潮, 40 多萬阿爾巴尼亞難民東移馬其頓,更讓馬其頓的阿爾巴尼亞人,成為全國第二大的人口族群,共佔總人口的30 % 以上(馬其頓總人口為212 萬左右)。
然而,由於馬、阿兩國自冷戰時代開始便互不往來(阿爾巴尼亞曾實施長年的鎖國政策),馬其頓的執政者亦基於境內阿爾巴尼亞人的語言(印歐語系)、宗教信仰(伊斯蘭為主)均與馬其頓人不同,加上大量難民湧入,因此不只社會上兩族人鮮少往來,馬其頓政府在政策上亦開始打壓該族,諸如阿爾巴尼亞族群不得公開使用阿爾巴尼亞旗幟;公務機關不得使用阿爾巴尼亞語言等。
而阿爾巴尼亞人長年於體制內抗爭要求「平權」未果下,到了2001 年,在相對激進的組織「阿爾巴尼亞自由戰線」(Alba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, NLA)帶領下,發動「內戰」,對馬其頓軍警進行武裝攻擊。近六個多月的武裝衝突,造成雙方軍隊均有數百人的死傷,平民死傷近千,更有十萬餘人因此流離失所。最後衝突雖然在北約介入調停下結束,雙方的仇怨卻因此更深。
最鮮明的例子,是 2017 年馬其頓新上任的總理佐蘭.薩耶夫(Zoran Zaev),因2016 大選時聯合阿爾巴尼亞政黨形成國會多數,取得政權「政黨輪替」,卻遭受境內部分馬其頓人的激烈抗議,甚至因國會選出阿爾巴尼亞裔的議長,遭抗議民眾闖入議場,薩耶夫本人被打得頭破血流……。
走訪阿爾巴尼亞裔為主的城鎮泰托沃(Tetovo)
「你真的要去泰托沃(Tetovo)喔,還是要小心一點喔,你的長相太明顯了。」
就連我的馬其頓沙發主,聽到我要去 Tetovo 這個超過半數居民都是阿爾巴尼亞人的城鎮時,也略帶擔心地叫我要「注意安全」。
結果,跟她道別半個小時後,我就搭到了一台載我直達目的地的便車——車主是個阿爾巴尼亞裔的警察。
馬其頓境內,像Tetovo 這樣阿爾巴尼亞族人口很多的地方,同一個城鎮內,就會「自然地」分成「阿爾巴尼亞人區」跟「馬其頓人區」:雙方涇渭分明,很清楚「界線」,馬其頓人平常不會沒事跑到阿爾巴尼亞人的區域;反之亦然。
而像我這樣「完全狀況外」的旅人,常常不知不覺地從馬其頓區晃到了阿爾巴尼亞區,我唯一能分辨的差別,可能就是店家招牌上的文字吧⋯⋯用拉丁文字母的,基本上是阿爾巴尼亞人;用像是俄文那樣西里爾文字母的,則是馬其頓人。
一天,我在市郊邊緣,被馬路邊的羊群和牛群給吸引住了——我停下腳步,看著那些牧羊人們趕牛羊進貨車。馬其頓真的是一個「很不歐洲」的歐洲國家:在首都市中心時,常看得到牧羊人牽著4 、 50 隻羊在大街小巷穿梭,也可以看到吉普賽人駕著驢子在大馬路上撿回收……。
結果我才剛停下來沒多久,就被一群小孩給纏上,每個人都劈哩啪啦的要跟我講話,我試著用破碎的馬其頓語跟他們聊了一回以後,他們跟我說: 「不對,我們是阿爾巴尼亞人!」然後急著要教我阿爾巴尼亞的語言……。
「Fa le min de rit」小男孩慢慢的念著,讓我跟著他覆誦:「Faleminderit.」
「罰你們跌裡特?」我結結巴巴的唸完這個詞……這個語言的「謝謝」,音節也太長了吧!
他們接著很熱情地帶著我去看羊、看牛、爭相在我面前表演唱歌、跳舞跟武術。 (話說這群阿爾巴尼亞小孩竟然在唱 Despacito……)
我拿起相機示意要給他們拍照,那些小男孩們全部簇擁在一起,然後雙手拇指互扣,交疊起來用手背對著我,一起擺出了一個很有趣的手勢。
「這麼喜歡螃蟹嗎?」當時我心裡一邊想著,一邊笑著按下快門。
他們接著很熱情地帶著我去看羊、看牛、爭相在我面前表演唱歌、跳舞跟武術。
對彼此有著成見,卻同樣對我如此友善
由於在首都史高比耶時,聽到太多馬其頓人對我「善意提醒」,說著到阿爾巴尼亞裔的區域,必須小心當地人的「偷拐搶騙」,導致在跟眼前這群善良的孩子們一起玩的同時,我還是下意識地註意肩上的背包,甚至有點擔心會不會突然有人把我的東西偷走。
然而,就在我準備要離開的時候,真的有一個小男孩伸手抓了抓我的背包,嚇了我一大跳——但是他沒有把包包拉走,也沒有伸進去,只是等待我轉頭以後,細心地幫我把每個拉鍊都完全闔上。 (我常常會沒注意,留個 3 到 5 公分的空隙)
幾天下來,我發現我真的很喜歡 Tetovo,她甚至可以說是我目前在馬其頓最喜歡的一個城市。的確,我的亞洲面孔在當地真的非常突出,在其他大城市還好,但是在Tetovo 這邊,走在路上幾乎每個人都會想要跟我打招呼——有些是禮貌性的點頭,有些年輕的男生女生則會湊過來要合照,甚至有水果攤的老闆看到我經過,就送了一根香蕉給我。
但是,我還真的從來沒有被當成肥羊過。
分化與隔離,只會讓成見代代相傳
我還沒有遇過能夠順利溝通的阿爾巴尼亞人,還不知道他們對馬其頓人的看法。當然我知道,也許就像台灣人一樣,我們對待外國人,常常會比對待自己身邊的人好……我也知道,就算我遇到的阿爾巴尼亞人都很善良,也絕不代表「全部的」阿爾巴尼亞裔人都是如此。
但我認為,即便如此也沒關係——我很清楚自己曾經遇過許多對我很好的阿爾巴尼亞人;因此,就算之後我可能真的遇到了「很糟的」阿爾巴尼亞人,我也不會因此痛恨「整個」族群。
……其實,上面兩句話的「阿爾巴尼亞人」,我想都可以替換成任何一種「民族、國家標籤」,我相信意思也是一樣的。
雖然身為一個外國人,不太有資格對馬其頓這個國家中,兩個民族數十年累積起來的「愛恨情仇」說三道四。不過馬其頓跟阿爾巴尼亞人「分區生活」也就算了,竟然連學生也彼此隔離——馬其頓人的小孩早上去上學;中午放學後,換阿爾巴尼亞族的小朋友來到同一間學校上學,聽說連老師也都不一樣。
我不禁想起,文章開頭時,那位在吧檯跟我聊天的馬其頓高中男生——如果他在唸書時有個一起長大的阿爾巴尼亞裔同學,應該就不會講出這樣子的話了吧…. ..。
最後,也許很多人並不知道,所以在此附上阿爾巴尼亞的國旗。
看完國旗應該馬上就會明白,原來那些小男孩比的並不是螃蟹,而是雙頭鷹阿!